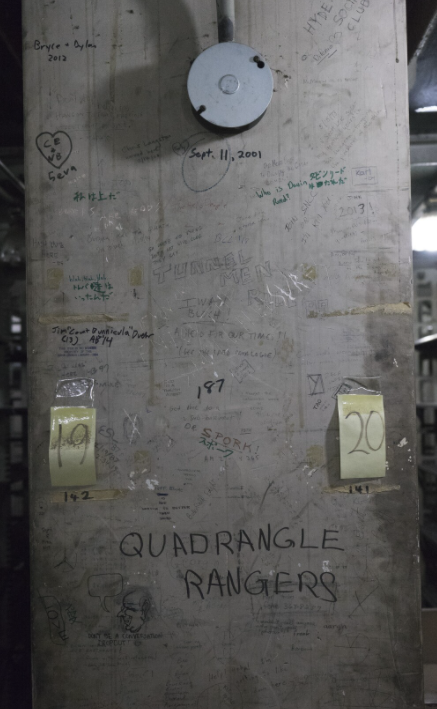下午四点一刻,我站在时间修理店门口,敲了三下门,没有回应。
这是我二十六岁时的事情,那时候正在经历一段充满差错的生活。之后遇上新冠,整个人像是腌黄瓜一样在家里发酵了一年半。我那位远在德国的导师让我过上了一种颠三倒四的日子。日日夜夜像一个沙漏一样反复不停,却总是不能尽兴地流向哪一边。同一个沙漏还时常挂在我的电脑屏幕——对着程序里的数字,我会出神地看上一个小时,就好像这也是我无聊工作的一部分。
而屏幕里的沙漏终究对我起了作用,我患上了干眼症,左眼止不住地流泪。起初是搔痒,之后是无意识的一两滴眼泪,最后是止不住的泪流,似乎这只左眼借给了世上某个想哭却必须忍住的人,虽然右眼仍属于麻木的我。几次流了满衣衫之后,我请了半天假去看医生。但是医生甚至没有检查,只是嘱咐少看屏幕,就放我走了。回到家,屏幕是不能看了,却不知道做什么好,总是忍不住想看看电脑、电视、手机。我想起可以看书,就找了一本来看,哪知道看了几页又流下眼泪来。这时候我才决定,应该出去走走了。
去商店街的缘由也是有的,搬家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块坏掉的手表,需要修理一下。表是二十岁生日时候父亲送我的礼物,一块宝蓝色表盘的机械表。父亲很熟悉我的喜好,特意选了一块设计最收敛简单的,塑料表带的手表。当时我还有戴表的习惯,虽然大多时候是解下来揣在兜里当作怀表。可惜这块表在我腕子上只随行了一个月,就让门把手在表面上划了一道痕迹。这痕迹说浅也确实很浅,只有佩戴者仔细查看才能发现,但是自从发现了,我就无法释怀,时常去摸表面,去寻这划痕,摸到的时候一丝的遗憾却又含着安心。这样下去心里总归不舒服,就收了起来没再戴过。至于为何发现它时候表带也断了,我就全无印象了。
商店街各类铺子应有尽有。这个地区在变成如今的流浪者营地之前,曾经是嬉皮士们聚集的时髦地段,在那之前许多年,这里还是一座独立的城市。来自北欧的移民建立了许多坚实的砖木房子,作为教堂和酒馆。待到我穿越这条街的时候,曾经的教堂也已经夷为平地成了酒吧。其他的店家更为省事,图书馆圆顶的砖房被直接改修成了露天酒吧,那间记录借书的柜台摆了十几种啤酒的喷头,管理员刷卡借出的是浓啤酒和热狗。消防局也变成了酒吧,俗气地挂了一个以此为玩笑的招牌,什么大火之类的话。花店变成了拳击场,这里可从没这么热闹过。我觉得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咖啡店变成了连锁咖啡店。这就像魔术师帽子里的一只兔子变成了另一只兔子,起初人们觉得没什么稀奇,等到许久之后才会想起来,从换兔子的那个时刻起,观众自己完全变了。有些变化留有痕迹,就好像消防局酒吧永远会是消防局主题,而咖啡店的取代悄悄然是一张革命。从记忆里回溯的时候,已然分不清两只兔子。或许从来也没有过两只兔子。
而有些改变尚未完成,唱片店关张后的店面已经空了一年许,里面木质的唱片架还刻着字母表分类,新的店家还没有来。几年前我向老板问询过秋吉敏子的唱片,老板答应我如果遇到帮我收购两张,在那之后还没有再来过,整个店却已经空了。隔壁古董家具店的桌椅柜子换了几批,而那个顶着鸡头的木立钟却还在显眼的位置,等着人带它回家去,只是没有人像找一张没有在美国发售的唱片一样,搜寻这样一座鸡冠立钟。
转过街角,我看了看时间。那块脏兮兮的手表比手机慢了二十来分钟,这些许年来只慢了二十分钟,或许说明这是快好表。但是仔细一看,其实是早就停了摆,恰好在了同一个时辰里。既然时候还早,我顺着斜街走到了水闸。恰好是鲑鱼洄游的时节,水闸的通水口里许多鱼在争抢位置。人类好奇心重,修了个玻璃墙隔着屏幕观看,就好像体育竞赛一样。广播里一个激动的声音给孩子做科普,讲鲑鱼的一生云云。鲑鱼从淡水的湖泊溪流中出生,到海里生活一辈子,死前一定要再回到出生的地方,产卵生育而死。我看着它们银灰色的鱼背,思索着约么它们在海里行的路比我这二十余年加在一起还多一些,却被困在玻璃墙后面由我审视。“在这一生的终点”,那个激动的声音继续讲解,这些鱼死在了出生的地方,它们带来了海水里的养分,滋补了生态圈,变成了食物。孩子们赞叹大自然的精妙设计,而我感到有些虚无缥缈,原来这几千公里的旅程终究是有如此的句号。
穿过水闸,路过码头改成的餐厅和旅店改成的健身房,我终于找到了地图上标的修表匠的铺子。这间铺子并不叫修表店,而是时间修理店。时间如何修理呢?坏掉的从来不是时间,而是衡量时间的工具,钟表会坏,手机会失去信号,按着心跳数秒会错过一两拍,这之中似乎时间并没有什么过错。
我又敲了三下门,依旧没有人答应。弯下腰看,半地下室的窗子上贴了一张字条,写着“如果您的钟表有健康之忧,请打电话联系”。之前在超市听见一个女人向收银员抱怨修表匠的脾气,好像是不喜欢某些词汇,我猜这“坏”就是其中一个被痛恨的词了,要用健康之忧来代替。时间修理店,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医疗机构。图书馆那枚宣布闭关时间的钟表,现在记录着酒吧里下午打折时段的开端,不知道它工作得健康吗?古董家具店那些破钟,和皮沙发、主人的老狗、北半球的冬季一起慢慢沉下去,沉得越来越慢,它算是健康吗?至于鲑鱼们呢……我的左眼又流下泪来。
依旧没有人答应,我给字条上的电话拨了过去,依旧没有人接电话。但是电话里提供了更多信息:时间修理店,一百多年的修表匠家族,修理我们的时间健康。请留言,我们会依照您的时间安排访问。
回家路上我经过了一座大桥,火车轰隆隆过去,所见与所听甚至有些错位。我不禁想起鲑鱼和魔术师的兔子来。修过的钟表,就算重新追赶上我们,也终究变化了一部分,失去了一部分。我想起很多个长夜里,我的小挂钟哒哒走秒的声音,令人抓狂地精准。我拔掉了时钟的销子的时候,是谁的时间错位了呢?
时间修理店,如果真如其名,不修理钟表也不意外了。这是我与它的第一次相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