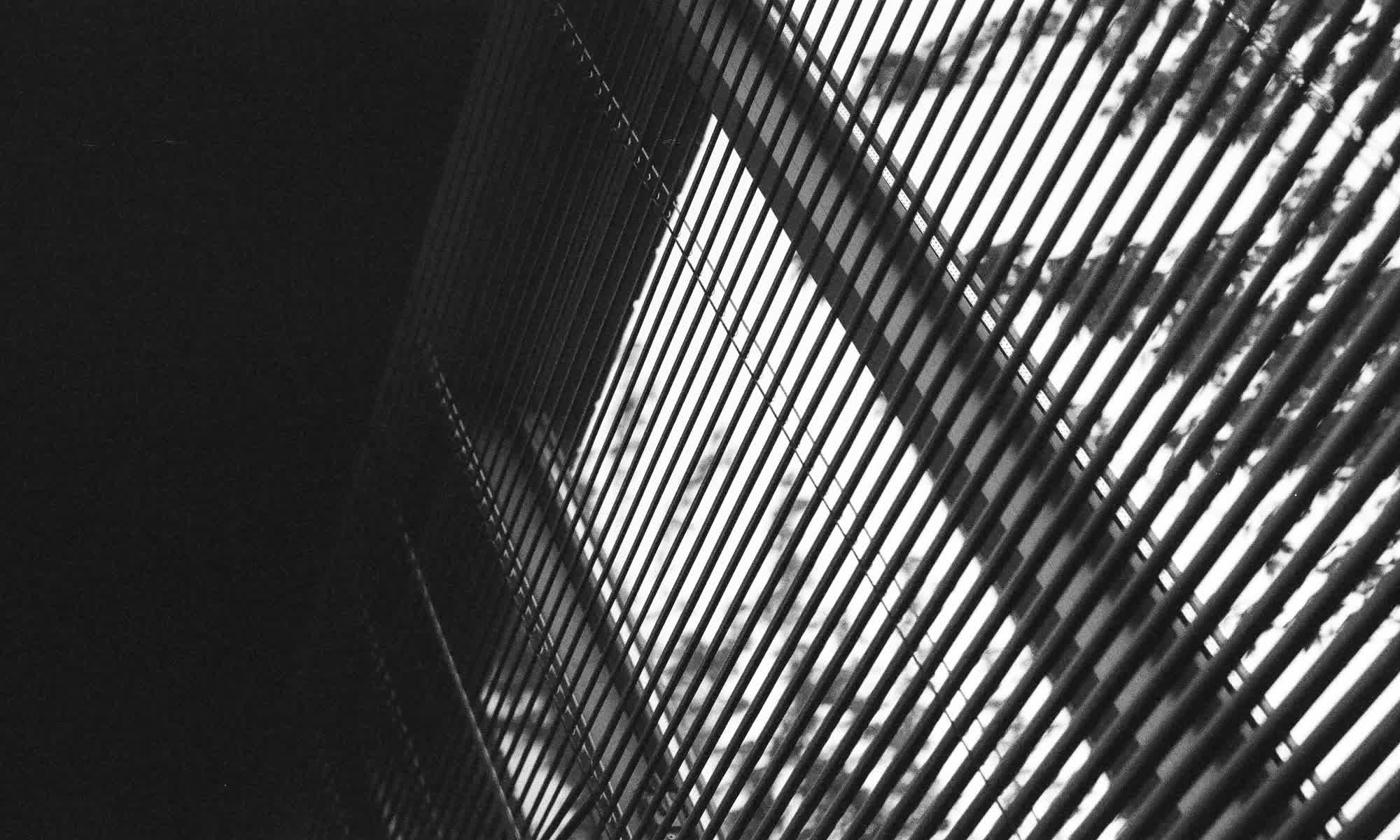今年早些时候,我买了一台小小的Minox 35 ML相机。可以折叠的镜头隐藏在机身里,整体就像一个钱夹子一样大小。黑色的机身上,快门是一个俏皮的橙色小键,吸引了我的眼睛。机体半嵌在革质手感的保护壳里。为了小巧设计,进片装置是短短的一小根杆,需要推两次才可以进一幅底片,由于这个设计,在1974到1996年间,这台机子都是最小的35mm胶片机。
购买现场匆忙,我没有拆开机看内部。回家打开才发现其实有快摄完的测试胶卷。许多老相机的买家会拍摄一卷黑白胶片自己冲洗出来,看看相机的镜头有没有外观难以发觉的霉斑。可惜这台机器被我打开的一瞬间,直接曝光了几幅。我连忙把机子扣上。其实也没必要急忙,以光的速度,打开的一瞬间早已经趁乱把影像毁灭了。之前的主人到底照了什么呢?我很好奇。
今天终于把这卷胶片冲洗了出来,这一卷是自己DIY封装的,用了其他胶片的壳子,贴了歪歪扭扭的写胶带上写了伊福德HP5+。总共24张,有七八张拍摄的山间湖泊,两三张灯火,一张有号牌的汽车,两张模糊的人影,是一个大胡子的人——这台机子的最近对焦距离在0.95米,而这个人很明显地站得太近,虚焦了——被我意外曝光前的两幅拍摄的是同一间书房,有双屏的工作台,和播放着电视剧的古早电视。
我很好奇,这几幅之间发生了什么?我又曝光毁掉了什么?一个愿意拍测试卷的人,一个愿意拍摄自己车牌的人,为什么要把相机转卖掉了呢?书房的电脑屏幕,电视剧里有什么线索么?书房有两盏宜家的Not灯,主人的身份是什么呢?房间的朝向是南还是东呢,我用手头简单的扫描仪试图放大这张照片…………
这是一篇我读过的小说,我对自己说。一个做翻译年轻人拍了一张对别人而言私密的照片,在暗室里将其放大。在工作的打字机对面挂起来,对着它填补这一幅之外的故事和人物的关系,摸索那一瞬间的前后事件。之后再放大一些,再丰富这个故事。再放大一些……这是科塔萨尔的《Las babas del diablo》,后来被米开朗基罗·安东尼奥尼拍成了电影《Blow-Up》,意思是“放大”,中文不精确地翻译成了“春光乍泄“。
故事的最后,一切都是一场虚妄。并不是梦,只是毁灭了的现实。奇怪的是,最终你手里还是会有这么一张照片,它的每一个像素都是真实的。